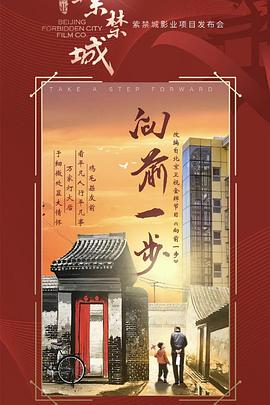◎桑梓
当地时间5月13日晚,加拿大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在安大略省去世,享年92岁。
艾丽丝门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之一。据新闻说,她在去世前十年饱受失智症困扰,这使我想起了同样患上失智症的侯孝贤。艺术巨人敌不过时间的风蚀,但他们已经在世间留下快乐影子之舞。
别再说她是加拿大的契诃夫她是艾丽丝门罗
早在2012年,门罗就已经宣布封笔。2013年,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奖评委们称她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在她还不被中国读者熟知时,出版商给出的噱头是加拿大的契诃夫。这一说法来自于造词大师詹姆斯伍德。
但现在,我们不再需要这样老掉牙的称谓,一个女人,不需要被称作某个男作家的化身。在诺奖授予她十年以后,门罗已经被中国的文学爱好者所熟知,她也是近十年来销量较好的诺奖得主之一。在她笔下,女性逃离与回归时的复杂心境得以显形,一间看似平淡的屋子也能上演着女性命运般的复调悲戚。当古板批评家呼吁当代作家把格局撑开,效仿历代先贤如托尔斯泰、狄更斯、莎士比亚时,门罗反其道而行,在短篇小说这条路上一意孤行。谁说女人的内心就比男人和马的战争格局小?谁说写短篇就一定比长篇小家子气?门罗将这些庸俗成见通通摒弃,不是以嘲笑的方式,而是以巨大的冷静和耐心,就像女人搭建和守护属于自己的房屋。
房间是门罗小说中的重要象征。在《重重想象》中,玛丽麦奎德想象自己是房间里的另一座孤岛。大部分时间,她坐在风扇旁边,风扇似乎已然筋疲力尽,搅动空气的模样仿佛是在搅拌浓汤,而她的声音充满了苍凉而婉转的控诉之声;在小说《苔藓》中,女主人公斯泰拉住在休伦湖旁白垩岩上的一座木屋,她干农活,种蔬菜,不再按照男人的审美来打扮自己;在《办公室》中,门罗干脆写道:房子对女人的意义和男人不一样。她不是走进屋子,使用屋子,然后又走出屋子的那个人。她自己就是这房子本身,绝无分离的可能性。
有意思的是,当门罗回击他人质疑其重复写作时,她也用了房间这个喻体:更像是所房子,你进去,然后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你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房子里。每次回去,这所房子这个故事,都比你上次看到的包含更多内容。它有一种自身的存在感,一种自身存在的必要性,而不是仅仅为迷惑你或者给你提供落脚之处。
当女人决定出走
门罗本名艾丽丝莱德劳,出生于安大略省休伦县温海姆镇。父亲饲养狐狸和家禽;母亲是一名乡村教师,罹患帕金森综合征。为了分担母亲的担子,门罗早早学会承担家务。在她8岁时,加拿大卷入二战。战后,她去了西安大略大学读书。高中毕业那年,她的学业成绩位居班级第一,荣获西安大略大学奖学金。大一时,她攻读新闻专业,大二转入英语系那是她这辈子少数不用做家务的日子。
好景不长,她在20岁时与大学同学吉姆门罗结婚。二人移居到温哥华,先后诞下四个女儿,其中二女儿出生当天不幸夭折。在日后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门罗回忆,自己当初早早结婚是为了避开长辈的压力,想着赶紧解决掉这个问题,他们就不会再用这个事情来烦我。然后,我就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我的人生就会开始了。她和吉姆在温哥华岛南端的维多利亚市开了一家小书店,在带娃之余,她抓住空余时间写作。她试过一直写到凌晨一点,第二天一早六点起床。她在熬夜过度时会想:我可能要死了。我会心脏病发作,但就算我死了,我也已经写出了那么多页的东西。
门罗自1960年代开始写作。彼时世界正处于新的动荡,反越战运动、五月风暴和平权运动交替进行,门罗则在1968年出版了首作《快乐影子之舞》,那一年她37岁。41岁,她决定和丈夫离婚,成为全职作家。在81岁封笔时,她已经出版了14部作品,包括13部短篇小说集和1部仿佛故事集拼贴的长篇小说。
跟阿特伍德有明显的写作更迭期不同,门罗一出手就很老辣,她不会为了迎合市场而添加猎奇糖精,也不会刻意为了彰显自己求新,就去写作并不熟悉的题材。门罗并不是博尔赫斯那样的博物想象型作家,她贴着生活经验而写,力求轻盈、准确、生活化,把作者的姿态埋得很低很低,犹如摄影机对人际交往的注视,在那猝不及防的刹那,撕开关于生活本质的血口。
1970年代起,门罗开始为《纽约客》撰写专栏。她精巧的短篇吸引来眼尖手快的同行,但由于短篇不如长篇在推销上更有噱头,早期门罗仍处于相对小众的位置。直到她的小说攒到一定地步,读者们赫然发现:他们喜欢的诸多短篇,原来都出自同一个人。
她的短篇犹如小长篇,让读者感受到庸常生活里的巨大张力。在对普通人物的描绘中,她娴熟运用跳接、隐喻、象征、对照等手法,将一个人的命运浓缩在很短的时间。在她的小说中,主人公一直在逃离某种秩序,婚姻的、家庭的、道德的甚至整个社会的。这些女性也许没做出激烈行动,但内心已是千回百转。在短篇《亮丽家园》中,门罗反思了现代生活对于个体的驯服;在《漂流到日本》中,她描绘了登上去多伦多的火车的女诗人格丽塔;而在《太多的欢乐》中,她再一次提及房间与女人的关系:男人走出房门的时候,他就把一切都丢到了脑后而女人走出去的时候,却把房间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带在了身边。
为真实而战
在门罗写作的年代,短篇小说家一度不受重视,阿特伍德就为此替门罗鸣过不平。而门罗频繁书写女性生活,极少书写战争、史诗等宏大题材的选择,也一度让主流批评家颇有微词。门罗一度被贴上了家庭主妇的标签,有评论说她的作品太过家庭化。但门罗不在乎这种狭隘之见,她写关系,写空间结构,写人心之谜,她忠实于写作正在面对的生活。有人曾玩笑称诺奖颁给短篇小说家是恶作剧,而门罗是诺奖得主中罕见的以短篇小说为主要成就的作家。她坚持写中短篇,写女人们的各种困惑。阿特伍德认为:门罗对于社会阶层和细枝末节极为敏感,她笔下的人物习惯于严格审查自我的行为、情绪、动机和良知,并寻找不足之处。
阿特伍德同时指出:门罗故事中的作家主人公都蔑视和不信任艺术作品矫揉造作的一面。应该写些什么?该如何写?艺术作品中有多少是真诚的,又有多少不过是装满廉价花招的包袱复制人类,操纵他们的情感,做做鬼脸?
随之,阿特伍德归纳了门罗小说的一个重要母题为真实而战。门罗笔下的人物反抗着令人窒息的重负,渴望挣脱强制性的行为规则、噤声不语和精神压抑。阿特伍德总结道:在工作优秀但矫情且内心麻木和表现糟糕但真实且活力四射之间,门罗笔下的女性可能会选择后者;要不然就是,如果她选择了前者,便会自责于自己的圆滑世故、背信弃义、诡计多端、阴险狡诈和无理取闹。在门罗的作品中,真诚绝非最佳策略:它根本不是策略,而是如空气一般必不可少的元素。
在爽文流行的当下,门罗的小说初读起来并不爽,甚至可能给你添堵,但她有一种魔力会召你回来。起初,她看起来只是不紧不慢地谈论一段生活,你仿佛置身于多雾的天气,眼前是辽阔的港湾或清冷的小镇。可是随着叙事的推进,当门罗将她想要讲述的情境一点一点剥开,你就有可能被突然击中在一个他人睡去的夜晚,兀自惊心动魄。
如果你想要一览更完整的门罗图景,除了《亲爱的生活》《逃离》等虚构小说集,门罗的自传性小说《岩石堡风景》也值得阅读:从文海姆镇维多利亚路尽头的住宅,到9英亩的休伦县农庄;从房子内部的许多转角和奇怪的小台阶,到门罗的父亲罗伯特莱德劳逃离失败的故事,《岩石堡风景》浓缩了太多作家本人生命的影子。
颇为有趣的是,当门罗获得诺奖的消息传到故乡时,并不是谁都乐意恭喜她。评论者王芫在谈论门罗时就提到,当时《多伦多星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艾丽丝门罗从哪里找到她的故事》。文中谈道:一位来自门罗家乡的女士告诉作者:自己的母亲当年读过门罗的小说后,认为艾丽丝门罗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理由是:她写的既不是小说我们能认出书里的每一个人;又不是纪实书里的每一个人都比实际要坏。
比方说:1939年,温海姆镇发生过一起18个月大的婴儿被开水烫死的事故。结果门罗的短篇《死亡时刻》里也写到类似情节,就连一些细节也跟现实版本一致,这导致死去婴儿的家属和门罗发生过争议。据说婴儿的父亲带着枪来找门罗的父亲,要求门罗承诺不再写家乡的故事。门罗则认为这些指责是不实之词,她写的是小说,并不是非虚构,她使用了一些新闻作为故事背景,但人物早已经过了艺术加工。
笔者不想因为门罗去世就避讳这一争议,作家是人不是神,对一个作家的神话或选择性叙事都毫无必要。当作家选择忠实于她的精神世界,后人对她最好的纪念就是尽可能接近那个真实的她,去读她不同阶段的作品。
而如今,斯人已去,像是耳边一阵巨响,却是那么平静。门罗去世这一天夜里,我久久未眠,一直到凌晨。这篇纪念性质的短文也正写于这个长夜。于我而言,门罗去世,起初带来的是惊诧与失落,但很快会复归平静。有一种人的死亡并不需要郑重其事的伤感,因为作品已经令她永远在场。哪怕她离开了,而她的声音永远存在在每一个平静生活里准备裂开又勉强修补的洞口里,在每一间并不属于自我的房间,在每一次坐在车上渴望逃离又松手的时刻。艾丽丝门罗永远在场,就像一百年后人们还在谈论着弗吉尼亚伍尔夫。